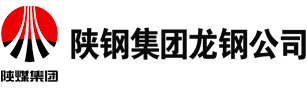铁矿石作为钢铁工业的“粮食”,是制造业、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防安全不可或缺的战略性原材料。根据《全国矿产资源规划(2016-2020年)》,中国已将铁矿正式列入战略性矿产目录。2024年,中国累计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约12.37亿吨,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超过80%。可见,无论从制度层面还是事实层面,铁矿对中国都具有战略属性。
近年来,伴随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紧张、大国战略竞争加剧,以及去风险化、供应链阵营化、产业链本土化等趋势加速演进,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铁矿所面临的法律环境日益复杂。一方面,传统法律风险(如政策变动频繁、矿业权属不清、社区冲突、环境合规等)依然普遍存在;另一方面,新型制度性风险(如ESG合规壁垒、价值观导向的供应链排斥、资源民族主义政策工具化等)正深刻重塑投资规则。在此双重挑战下,系统识别并统筹应对传统与新型法律风险,已成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、提升产业链韧性的关键任务。
传统法律风险:
基础性但不可忽视
尽管国际格局深刻变化,传统法律风险仍是海外铁矿投资中最常见、最直接的挑战,若没有充分识别或处理不当,足以导致项目失败。
一是东道国法律体系不健全或变动频繁。许多铁矿资源富集国[如几内亚、刚果(金)、塞拉利昂、利比里亚等]法治基础薄弱,矿业法律体系不完善,政策执行随意性强。政府更迭常导致既有矿业合同被单方面要求重新谈判、变更甚至终止。例如,几内亚在2021年政变后对西芒杜(Simandou)铁矿项目发起全面审查,要求提高国家持股比例和税收贡献,令投资者措手不及。此类政策的不确定性极大削弱了投资的可预期性。
二是矿业权属不清与准入限制。部分国家对外国投资者设置严格的准入壁垒,如限制外资持股比例(要求本地控股)、禁止外资参与勘探阶段或对战略矿种实施特别审批。更严重的是,存在“一矿多授”、权属重叠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授权冲突等问题。中国企业若未在尽职调查阶段厘清权属链条,极易陷入产权纠纷,甚至被认定为“非法开采”。
三是环境与社区合规风险。铁矿开发涉及大规模土地占用、水资源消耗、粉尘与噪声污染及尾矿库管理。若未依法完成环境影响评估(EIA)、未制订生态修复计划或忽视原住民权益,极易引发社区抗议、行政罚款甚至项目关停。
四是外汇管制与利润汇回障碍。部分资源型国家为防止资本外流,对外资企业利润汇出、资本撤回设置严格限制。企业虽实现账面盈利,却无法将资金汇回国内,严重影响投资回报率与现金流安全。此外,本币贬值、汇率波动也可能导致实际收益大幅缩水。
五是争端解决机制执行难。即便投资协议中约定国际仲裁(如ICSID或UNCITRAL),若东道国非《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》(即《华盛顿公约》)缔约国,或其司法系统不承认仲裁裁决,企业即便胜诉,仍可能面临“执行不能”的困境。部分国家甚至通过拖延司法程序、设置行政障碍等方式变相抵制裁决执行。
新型法律风险:
战略竞争下的制度性挑战
在传统风险基础上,当前国际格局演变催生了更具系统性、隐蔽性和政治性的新型法律风险。
资源民族主义与政策“武器化”。越来越多资源国将矿产视为国家发展与外交谈判的战略工具,通过立法或行政手段强化控制。例如,印度尼西亚以“禁止原矿出口”倒逼外资建设冶炼厂的模式正被多国效仿;玻利维亚、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则推动锂、铜等矿产国有化,未来不排除向铁矿延伸。此类政策名为“国家利益”,实则构成对投资者权益的实质性侵蚀。
供应链“阵营化”与合规排斥。美欧正构建以“价值观”和“可信度”为基础的供应链体系。欧盟《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》(CSDDD)要求企业对其全球供应链进行人权与环境风险排查;美国《通胀削减法案》(IRA)则通过税收抵免激励“友好国家”来源的原材料。若中资铁矿项目被认定存在ESG违规或与“非友好政权”关联,可能被排除在欧美市场之外,间接影响下游钢铁出口。
产业链“本土化”为强制要求。为提升本国产业附加值,越来越多东道国立法要求外资矿业项目必须进行本地加工、使用本地劳工、采购本地服务,甚至强制技术转让。此类“本地含量要求”虽不直接违反WTO(世界贸易组织)规则,但显著抬高了投资与运营成本。若投资协议未设置豁免条款或补偿机制,易引发履约争议。
ESG与“绿色壁垒”制度化。全球碳中和进程推动铁矿行业绿色转型。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(CBAM)虽暂未覆盖铁矿石,但已覆盖钢铁产品,倒逼钢厂要求上游供应商提供低碳铁矿或碳足迹数据。若铁矿项目未采用电动矿卡、可再生能源供电等低碳技术,或缺乏IRMA(负责任采矿保证倡议)等国际认证,将面临融资受限、客户流失等风险。
国际投资仲裁的政治化倾向。近年来,部分国家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(ISDS)持怀疑甚至敌视态度,阿根廷、玻利维亚等国已退出ICSID(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)。同时,西方主导的仲裁庭在裁决中更强调“公共利益”“可持续发展”等价值判断,传统投资者保护条款(如公平公正待遇)解释趋于限缩,维权难度加大。
综合性防范策略:
从合规到战略协同
上述双重风险的叠加,源于三重结构性矛盾:一是中国企业长期“重资源获取、轻制度适应”的投资惯性,过度依赖政府关系而忽视规则建设;二是资源国发展诉求(如工业化、就业、财政收入)与投资者权益保障之间的张力;三是中国“走出去”模式与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规则之间的制度鸿沟。在“去风险”而非“脱钩”的新叙事下,法律工具日益成为地缘竞争的隐性战场。
为有效应对双重风险,中国企业需构建“传统+战略”双轮驱动的法律风控体系。
一是深化尽职调查,引入多维评估。投资前期尽调应超越传统法律审查,纳入地缘政治稳定性、BIT保护强度、ESG合规成本、供应链准入风险等维度。优先选择法治健全、与中国有强BIT保护且未深度卷入西方“去风险”体系的国家(如部分中亚、东欧国家)。
二是优化投资架构,强化国际法保护。通过在新加坡、荷兰、卢森堡等与东道国有强BIT保护且税收友好的司法管辖区设立中间控股公司,提升法律保护层级。在投资协议中明确约定稳定条款、公平公正待遇、充分保护与安全、自由汇兑及ICSID/UNCITRAL仲裁条款,并争取适用国际法或中立第三国法律。
三是构建全周期ESG合规体系。将ESG嵌入项目全生命周期,前期开展高标准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估;建设期采用低碳技术(如光伏供电、电动运输);运营期定期发布ESG报告,主动对接IFC(国际金融公司)绩效标准、赤道原则及IRMA认证,提升国际认可度。
四是推动“共赢式本地化”。变被动合规为主动融合,与当地政府共建港口、铁路、电力等基础设施;设立职业技能培训中心,优先雇佣本地员工;支持社区医疗、教育项目,将企业发展与东道国工业化战略深度绑定,降低社会与政治风险。
五是建立国家级协同支持机制。建议由商务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自然资源部牵头,联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、行业协会等,建立“战略矿产海外投资法律风险监测与应急响应平台”,提供国别风险预警、争端调解、政治风险保险、法律援助等一站式服务,形成“企业主体、政府支持、专业协同”的风险防控合力。
如今,海外铁矿投资已从单纯的商业行为,演变为关乎国家资源安全、产业链韧性与国际规则话语权的战略行动。中国企业必须摒弃“关系导向”“速度优先”的旧思维,转向“规则导向”“长期共赢”的新范式。唯有统筹应对传统法律风险与新型制度挑战,以法治思维驾驭地缘变局,方能在全球资源竞争中行稳致远,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资源根基。

杨贵生 王永慧(杨贵生系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,王永慧系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)